0.05毫米:薄如蝉翼,重于未来
发布时间:2024-02-01 信息来源:
一张膜,不到0.05毫米的厚度,能有多重?
如果它承载了一代人的心血、一辈子的坚持或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又有多重?
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换代,有些随往事如烟般地散去了,也有些却被时光描摹得越来越深刻。

代号:真空阀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沉寂已久的戈壁荒漠一声巨响,随后,欢呼声、掌声、脚步声、广播声如决堤潮水般涌向全国各地。
全国沸腾了。全世界也被震得摇晃。
然而,由于工作需要保密,有一群人没欢呼,没雀跃,只有心跳如鼓擂。他们的心跳,向来和原子弹研制事业的心跳同频。因为他们就是为原子弹装上“心脏”的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原子能事业,铀235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之一。然而,铀235与铀238属于同一元素,是任何化学方法都不能分离的“双胞胎”。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了一个核燃料工厂,关键技术由苏联专家掌握,其中一项管状分离膜元件可以将铀235与铀238分离,其完全由苏联提供,对中国人绝对保密。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分离膜元件停止供应。有人传言,苏联专家走后,中国的浓缩铀工厂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国的原子弹将胎死腹中。面对这样紧急和严峻的情况,党中央立即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原子弹的“心脏”——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各方面要为这项任务开绿灯。这项艰巨的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交给上海市和中国科学院承担。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曾言:“我们哪怕少活几年,也要把这个东西攻下来!”
1961年秋冬,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的共60多名攻关人员在上海冶金研究所集结,成立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成员大多在30岁左右,时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吴自良是技术总负责人。夜以继日的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终于在1963年的秋天有了结果,符合要求的分离膜元件试制成功。
没时间缓一口气,更紧张的挑战随即而来。
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第四次会议决定建立分离膜的专业试验厂,主要任务是中试生产甲种分离膜,并研制确定工业化生产设备和工艺,为规模化生产提供技术和人员保障。最终该厂取名为上海材料金属加工厂,厂址选在上海宝山,这就是核工业第八研究所前身。
原上海材料金属加工厂厂长张毅还记得他接到任务的那天,时任上海市“真空阀门”领导小组组长的许言把原上钢五厂党委副书记史久源和他约到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许言动情地说:“这件事要按中央的决心和市委的布置,用毕生的精力与你们一起投入这场新的战斗领域。”两人顿时觉得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身上,办公室里只剩下了喝水的声音。谈话结束时,张、史两人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有注目、握手、辞别。往回走的路上,张对史说:“看来我们俩这后半辈子都要放在这个事业上了。”
很快,宝山的一个废弃瓦砖厂就迎来了一群年轻人。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地、四个窑洞、两栋宿舍、一个车间、几间平房和唯一一条通向镇上的小路。此外,就是异常艰巨的使命。白手起家,与时间赛跑。他们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大量设备,解决了制粉、调浆、烧结、机械加工、焊接、后处理等一系列工艺问题。
中核八所原所长陈绍廉就是其中的一员。陈绍廉2023年已经88岁,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但眼睛特别地亮。曾经留学苏联的他被钱三强点名参与分离膜研制工作,被分到粉末组。那时候的他才25岁。“我觉得能干这份事业,很光荣,责任也很重大。”回忆起过程的不易,陈绍廉谈道:“金属粉末有毒有害,接触空气就燃烧,同志们做这项工作其实是面临着生命危险的,部分同志还中过毒。”实验人员全副武装,白大褂、手套、防毒面罩……一站就是一天,其间除了吃午饭,都不外出。
“我们那时为了搞出来原子弹真是不惜代价。”说到这里,陈绍廉的语调高昂起来。后来才知道,他的心脏不好,还装着心脏起搏器。
同样说到这句的,还有也担任过中核八所所长的梁明信。
“刚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知道去‘搞尖端’,国家需要,我就来,没管太多。”回忆起那段岁月,如今,已经86岁的梁明信忍不住感叹。他原本学电力专业,厂里分配他负责膜管焊接工作,他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分离膜像纸一样薄,十分脆弱,得用缝焊机进行焊接。但是,那时候国内研究缝焊机的只有很少几人,缝焊机也很不稳定,经常脱针。那个年代,一根膜管相当于一个人4个月的生活费,缝焊若是出问题就直接报废。为了保证分离膜质量达标,操作人员需要时刻盯着机器运作,从上千个产品中仔细辨别、挑选,“通过肉眼是看不到焊缝的,到后来,有的同志已经锻炼到用耳朵就能听出来机器什么时候脱针了。”
与预想的不同,关于生活条件的艰苦,他们并未谈及太多,反而强调了中央和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照顾:“我们这个项目真的是一路开绿灯,我们向其他单位请求帮助,有的单位甚至放下手里的工作,以协助我们为重。”梁明信还补充了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那时候还是困难时期,但我们可以吃到潜艇士兵吃的营养餐,里面有大虾,那可是周总理都吃不到的东西。”
“856”的岁月
草地茂盛、枯萎,再茂盛、再枯萎。对于他们而言,除了睡觉时间,就是工作时间。1964年2月,因设备问题,上海金属材料加工厂迁移到嘉定,新厂址代号856。
为了尽早成功,全厂一刻不敢停,边设计、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终于在1964年5月,成功中试生产出甲种分离膜,提前2个月交付第一批产品,经过鉴定,其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马上装配到专用工厂。由于出色的性能,分离膜于1965年开始批量生产,经过多年的实际投产,使用效果远远超出预期。这项成果在1984年被授予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又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现在看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工作严谨细致,这样做赢得了时间并且没有造成返工浪费。”张毅回忆。“当时国防工办的同志说,在这国防尖端攻关的项目中,我们是最好的范例之一。”
再紧迫,安全永远是他们心中一根绷紧的红线。谈到这里,梁明信又想起一件小事,那时候厂外一带还是土马路,但是为了给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提供防尘、清洁、安全的环境,工厂窗户不仅设计了双层玻璃,附近也全部改铺柏油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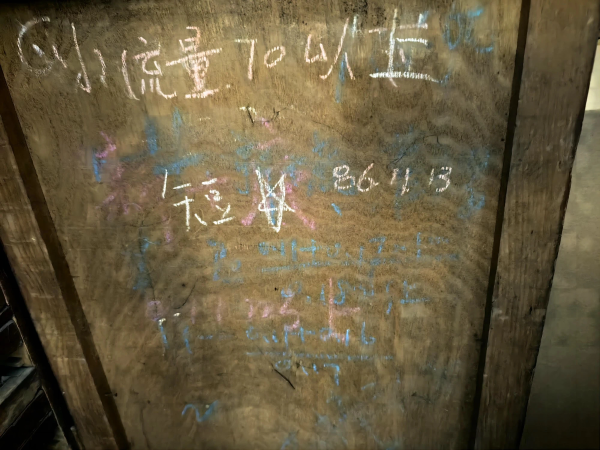
1964年,张毅带着刚试制出来的样品,怀着初战告捷的喜悦心情乘飞机飞往北京,向冶金部副部长王玉清汇报工作,提到部领导还没见过产品,所以随身带来了一只。王玉清听后立刻严肃起来,语气略重地问张毅:明明规定带样品要火车包厢军人押运,这次是几个人来的?怎么来的?张毅刚分辨两句,王玉清就发火说道:“飞机失事怎么办?样品丢失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张毅也认识到了错误,为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还有一次,跟车护送样品的厂技术科长王炳荣发现箱子里有数量不等的产品损坏严重,这一消息瞬间令大家神经紧张。产品内装和封闭非常仔细,专列火车车速、颠簸都有规定,损坏到底是如何造成的?王炳荣回厂后与成品仓库人员仔细研究,发现原来是管理成品装箱的冯祥东怕有灰尘,用吸尘器吸了几下,压力过大导致产品变形。此后,大家神经绷得更紧,再也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消息传到厂里时,由于生产还在进行,工作还需保密,大家虽然高兴得不得了,但都是闷着头庆祝。这时候,一种难言的感动在他们的心头激荡开,“真的是感谢党和政府的支持,特别还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国单位的配合!”陈绍廉和梁明信回忆起工作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不约而同地提到研制分离膜就是中国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型。他们其实早就笃定,这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因为我们早就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干不成就一直干,直到干成为止。”
直到1979年8月,856工厂先后研制、生产了五种分离膜,为我国“两弹一艇”成功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低迷中的坚守
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军工企事业单位发出“军转民”号召,“部里领导审时度势,提出了这个方针,但这对八所来说,又是一个难题。”说到这里,陈绍廉刚放松下来的腰又直了直。
改革的春风开始徐徐吹动。1983年,856厂由中试工厂升级改制为“核工业部第八研究所”。为推动八所由生产向产研结合转型,破解科研人员极度缺乏的难题,原核工业部从相关科研所专门调动了十对夫妻为主的多名专家学者充实研发力量,为此上海市特批了几十个“落户”指标。
但相比春风拂面的温暖,八所首先感受到的是一阵透骨的寒意。“有一段时间没活干,工资都发不了了。”目前已退休的科技工作者庄人杰想起初到所里时,正好赶上这一波震动,熟悉的研究不能做下去了,“我们这群人已经来上海了怎么办?那就要积极投入到军转民的活动中,这也是国家需要的。”
在这阵时代掀起的转民巨浪中,很多单位都没能挺过来。盛极一时的八所也跌入谷底。
但即使当年那颗原子弹爆炸的云烟渐渐淡去,回声已经平息,但他们还是那群热血到不计代价的人。他们继续排除万难开展过滤膜研究。

陈绍廉回忆起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俄罗斯有一家单位做的折叠机和过滤膜都非常好,正好又赶上随综合民用科技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陈绍廉就和团长周渊泉商量去实地看一看,担心外事方面一个人去不合适,所以请科技局处长王德明一同前往。1992年,苏联刚刚解体,秩序如沙堡般土崩瓦解,社会到处一片混乱。“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这怎么办?那也要去!”考虑到可能遇到危险,陈绍廉一行最后辗转联系到当地一位警察,花了50美元请他开车把他们带了过去。“当时那种情况,没有警察是过不去的。”那种紧张心情,陈绍廉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所幸陈绍廉向那家单位的副总经理介绍了中核八所的相关情况,对方非常感兴趣。1993年,中核八所正式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调研了氟膜、尼龙膜、聚偏氟乙烯膜等,并看中了一款折叠机,“10万元买折叠机、纵焊机、环焊机、端封机全套设备,这不算太贵。”因为那时候,美国一家公司曾开价,一台折叠机卖100万美元。合作推进得很快,1994年就签订了合同,同年10月份,八所的设备就配齐了。“他们的设备在我们国内确实是最好水平,我们也很快进行了学习吸收,后面又对其进行了改造。”陈绍廉又指着调研时的老照片,用俄语熟练地念出了每个老朋友的名字。
“机器设备有了,过滤膜也不能总是靠外面买来。”1991年,国际先进水平的气体除菌膜是聚偏氟乙烯(PVDF)材质的平板膜,但谁也没见过这种膜的生产设备,所里决定从有限的技术资料中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设计。通过2年多上千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疏水性PVDF膜。这种膜的诞生,打破了美国公司的垄断,广泛应用于发酵、食品、生物制品等行业的气体除菌过滤。1999年,PVDF膜及滤芯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每一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八所从不随波逐流,总是仔细看清每条道路的沟壑险难,才迈开大步向前走。“有一次领导带我们去美国考察,正在考虑一个几千万美元投资的项目,那个项目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但是——”,陈绍廉顿了顿,又清了清已经有点沙哑的嗓子,继续说道:“我们一看,他们才生产了十公斤,而且翻看生产记录,报废的产品还不少,合格率很低,我当时就和领导讲,这个项目不行。”陈绍廉考虑,如果真的谈成了这个项目,后续发展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八所后几代人就可能要背负一个沉重的贷款包袱,只图“短平快”的利润不可取,这个决定不能做。
被返聘到80岁的陈绍廉,一直关心着八所的发展,关心着过滤膜事业的进步。从镍烧结管到偏氟膜到四氟膜,再到全氟膜,中核八所脚踏实地地创出了一条新路子。这条路,中核八所也心无旁骛地走了40多年。
十年一张膜,每一张都薄如蝉翼,但浸透了青春、心血、梦想、情怀,却又沉甸甸的。
新时代再度“一鸣惊人”
如今的八所,坐标未变,但面貌已改。当年科研人员研制生产出镍烧结管的“东方红”大楼,如今也已换了颜色,很难再看出旧时的痕迹。
就在“东方红”不远处,一栋低调但颇具现代化气质的企业大楼静静伫立,遥相对望。它就是上海一鸣过滤技术有限公司,而它的前身是核工业第八研究所净化过滤工程技术中心。
2001年初整体转制后,一鸣过滤在过滤分离产品的研究开发、产业化生产、工程化应用和市场推广的道路上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同年,国产首款PTFE膜滤芯在此被研制出来。2010年,一鸣过滤又自主研发了亲水PVDF除菌级滤膜,并在国内率先攻克了全PFA滤芯生产技术。目前,一鸣过滤已发展成为拥有数十项相关国家级科研成果和专有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主编了5份国家标准和4份行业标准。
“我们的过滤产品应用前景非常广阔,是核工业、生物制药、海水淡化、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的重要战略物资。”一鸣过滤总经理吴昌飞大步流星地带着记者一边走一边介绍。
当前,核电厂一回路滤芯、疫苗除病毒滤芯、半导体2nm滤芯被称为过滤行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一鸣过滤研制了纳米纤维膜、平板式聚醚砜纳米过滤膜、2nmPTFE膜和滤芯。其中,“半导体用过滤器的研发和生产是一鸣过滤未来的重点建设项目。”吴昌飞补充。

如今,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产业。其中计算机、通信技术、智能设备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半导体元器件的技术突破。中国是最大的单一半导体市场,也是最大的芯片进口国,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过滤器虽然在半导体生产设备中占比较小,却属于关键核心设备。“目前国内半导体过滤器需求量很大,但90%的市场份额长期被外国企业垄断,我们想打破这种依赖进口的局面,过滤器研发的推进刻不容缓。”
自2020年开始,一鸣过滤公司调研和开发半导体过滤器生产设备以及摸索半导体过滤器生产工艺,目前已在技术上突破了PFA过滤器的折叠、焊接、检测、清洗、包装、灭菌全部生产工艺。
“不仅如此,应用于半导体过滤器的滤芯,膜孔只有几十纳米,都不能用普通颗粒来检测,”吴昌飞向记者展示了一瓶红色液体,里面是实实在在的黄金颗粒,“要用黄金纳米颗粒挑战法,它专门用于测定纳米级多孔膜的孔径。”国内极少企业掌握这种技术,一鸣过滤已经处于了领先水平。
“我们不仅继续在过滤膜的研制上加大投入,而且现在更系统化、市场化,因此也在产品的设备制造、检测、标准等各个环节上下了大功夫,”吴昌飞引着记者步入一间车间,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差点淹没他的声音:“比如滤芯的智能制造。”
国内研究过滤膜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做到连续化批量生产的少之又少,可能都不会超过十个。所以在吴昌飞看来,产业链的数智化是后起之力,在国内外的市场化竞争中都至关重要。
干净明亮的白色车间里,几条自动化机械臂正忙碌地进行着各种精细操作,“这是折叠式滤芯的生产车间,我们最终要做到全流程自动化,这是行业内的首创。”吴昌飞介绍,没有自动化设备的时候,需要六位工人在车间从早坐到晚,一天只能做600支折叠式滤芯,而如今,自动化设备一天能做1200支。不仅节约了人力,流程工艺的精准度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得到大大提升。此外,生产执行系统还可以将设备数据进行云端交互和存储,实现生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产品的全流程可追溯,提升了产品质量管控水平。
“还有,原来车间的环境很差,”吴昌飞又指向一旁的红外焊接机:“没有它之前,焊接加热的过程全是烟,工人就在旁边工作,吸入颗粒物对身体很有害,所以我主张一定要实现全自动化。”看着现在干净整洁的无烟车间,实在难以想象当时的工作环境。
另一间车间前,吴昌飞望着玻璃窗里一排带视觉机器人的全自动检测设备,对记者说:“每个滤芯都需要检测,所以我们的工人就需要不断弯腰再弯腰,这样一天太累了,而且他们心情也不愉快。”他顿了顿,接着说:“我们就是不要让工人弯腰。”
这句话,很响亮,很有底气。因为一鸣过滤已经在国内率先建成滤芯智能制造工厂,实现了智能组装、智能焊接、智能检测三大工艺,可以满足滤芯24小时连续生产。
除了数智化,走国产化道路也是吴昌飞一直以来的坚持。2016年,一鸣过滤从德国购入一台原装进口折叠机,刚开工不久,机器总是出故障。德国人说可以派专家来修,但一次要花费10多万元人民币。那段时间吴昌飞焦虑到睡不着觉。“靠别人肯定不行,国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吃透。”吴昌飞和团队自己着手分析,最后研究发现问题就在一根电线上。换了这根线后,至今8年时间,这台机器再没出过故障。如果不是自己钻研,不知道还要为一根线花多少个10万。“从国外把东西买来,不是为了花钱供着它,我要把这个技术吸收,变成自己的。”吴昌飞停下脚步,转过头说,“我们还要和国外企业去对标、去竞争。”
那段时间的辛苦在吴昌飞看来并不算什么,2017年才是他觉得最难的一年。一年时间里,他要编制3份有关除菌过滤产品的国家标准。彼时的产品概念、细节都存在巨大的行业争议,吴昌飞硬是花了1个月时间翻阅并翻译了全部的相关条文,研究出其中的设计理念和原则要求,又用2个月时间写出了标准的初稿,绘制了60多张设计图纸。
“每份标准都修改了5遍以上,逐字逐句地斟酌修订,甚至要考虑每一段话的标点符号。”为了完成好标准,吴昌飞每天“躲”在技术部一处小小的办公室里专心写作。为了赶稿,曾经3天3夜不睡觉,最终按时完成了国标的编写。“到后面,我甚至都有点耳鸣了。”吴昌飞的语气却很轻松。
大家都说,吴昌飞的身上有一种劲儿。
确实,是一种敢想、敢拼、敢超越的劲儿。这也是这个企业的劲儿,更是坚持做过滤膜事业的这群人的劲儿。
中核八所的院子深处,有一片原生态的树林,里面都是参天大树,有的甚至已过百年。平时很少有人关照,无畏风雨敲打、无畏酷暑严寒,它们只是默默挺直腰身,奋力向上生长,撑着顶起了一片天,然后轻轻投下了一片可以遮庇后人的绿荫。这片树林,无论何时总是不改颜色,一直生机勃勃。(中核集团官微)




 中国核工业官微
中国核工业官微 中核集团微博
中核集团微博 中核集团官微
中核集团官微